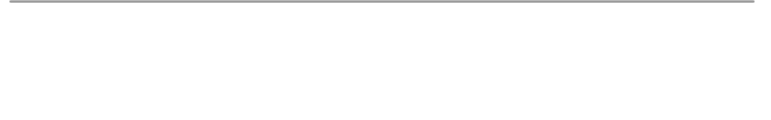|
川西北羌族探源——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2
代说,其主要依据是有的版本中《羌戈大战》的战胜者首领名叫“阿巴白构”,以及岷江上游地区氐羌人(戈基)的石棺葬文化消失于东汉。[4]关于这两点,笔者认为都可以有另一种解释,与“羌戈大战”隋唐说并不矛盾,详后。绵延数百年的“羌戈大战”在唐中叶结束以后,战败的原住葛延羌(戈人)迁往鹧鸪山以西,冉羌与先后内徙茂州的时、宕、居、涂、松、当、静、恭、柘州羌及向州羌、翼州羌、真州羌等在茂州地区安居下来,逐渐融合,统称“茂州羌”。
由《羌戈大战》可知,茂州羌开始筑城养猪,这是社会经济向半农半牧转化的迹象。《唐会要》、《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唐志》)又载,茂州产麻布、牦牛、干酪、麝香、狐尾、升麻、羌活、当归、麸金、丹砂、生马牙硝等;《寰宇记》载茂州羌人仍好弓马,衣褐羊皮貉及毛织物,产牦牛、马、羊,说明唐时畜牧业及山林副业仍占较大比重。
《羌戈大战》说,“阿巴木比塔”属羌靠白石战胜戈人,显然,《华阳国志》所载之“白石子”文化已由他们继承下来。传说中认为,就在这一古老的时代,白石崇拜有时在树丛中举行,有时在屋顶上举行,要有三根树枝和一块白石,在举行仪式期间,要祭祀一只羔羊,而且也必须是白色。遇到死人时,也要宰杀一只绵羊,宰羊是为了引导亡灵到阴间,对绵羊的尸体要进行解剖,以发现死者的病因。为了使一种病痊愈,必须将其转移到病人的替身身上,所以就需要焚烧一个用草扎的人。为了弄清病因,也使用了占卜术,被认为最古老的方法是用艾草炙绵羊的髀骨,这块髀骨应取自在树丛中或屋顶白石上进行祭祀的那只绵羊。[5]
二、左封羌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它分布在今阿坝州茂县、黑水县一带,但尚无人认识到这只是唐武德七年以前的情况。其实武德七年以后,左封羌之大部已分两支离开原居地翼州左封县(治今黑水县维古区),小左封一支南迁到今理县境内,贞观二年复内附,置为羁縻维州,《通典》及两《唐书·地理志》载维州有小封县,又《寰宇记》维州保宁县条云:“贞观三年,小左封生羌酋董屈占等举族表请置吏,因复置维州及二县。”俱可证;大左封一支南迁到今小金县境,成为千碉羌之一部,贞观五年复内附,置为羁縻炎州,州有大封县,亦可证。何以知左封羌之南迁是在武德七年?据两《唐书·窦轨传》、《册府元龟》卷三五七、《资治通鉴》卷一九记载,武德七年夏秋,吐谷浑会同翼州左封羌攻松州,唐益州道行台左仆射窦轨出翼州(时已自左封徙治翼针)岷山道往援,又令扶州刺史蒋善合自同昌出芳州道,期于松州会师。善合先期至扶州赤磨镇,遇敌力战,败走之,轨复追至故临洮郡境,斩吐谷浑王子贡,还击左封,破其部众。部众既破,则南迁势在必然。但此后由翼州改属悉州的左封县名仍沿用不废,表明该地可能仍有左封羌残部居住。小左封后融入维(威)州羌,大左封则于永隆后没于吐蕃,融入逋租羌。又《资治通鉴》卷一二载,刘宋文帝元嘉元年,西秦将军吉毗等南伐白狗、车孚、崔提、旁为4国。其车孚,疑即左封(拟音为chuofu)之异译。左封羌以定居农业为主,如贞观间有小左封羌居于羁縻维州,置有盐溪县,以村有盐溪,民得采漉,故名;[6]大左封羌徙居于今小金县平坦肥沃的沃日河中游,也是出于经营农业的考虑。
三、昔卫羌
向来无人知其所在,仅李敬洵《四川通史》第三册认为是在大左封东北,约当清代叠溪营昔鱼寨,在今茂县北部较场区。[7]考北周此地有蚕陵羌,唐初置为羁縻翼州翼针县,天宝间改卫山县,“卫山”疑即“昔卫山”之简称,如是,则李说可从,唐昔卫羌即北周蚕陵羌。唐中叶后融入茂州羌。翼州治所在今茂县北较场区,曾发现不少唐贞观间佛龛及造像,从题记中的施主姓名、官名看,多是州县官吏,羌民是否信佛则未可知。又《元和志》曰:卫山县北三十七里有笮桥,以竹篾为索,架北江水。《唐会要》、《元和志》、《新唐志》载,翼州产麻布、牦牛、麝香、当归、白蜜。反映当地羌人尚营半农半牧业,善治索桥,疑为氐羌类。
四、葛延羌
《四川通史》以“葛延”即“康延”,清曰“葛喇依”,地在今金川县安宁镇。任新建先生则以为即后来西山八国中的哥邻,地在今理县、茂县一带。[8]笔者同意葛延与哥邻有密切关系的说法,并进而认为葛延应当就是羌族民间传说《羌戈大战》中的“戈人”(或译为“葛人”),原住在会州汶山县(今茂县)及汶川(今汶川县)、金川(后改通化,今理县)3县河谷地带,今茂县、汶川、理县一带发现有不少据称系汉代“戈人”留下的石棺墓。他们在隋时曾受冉羌攻击,唐高宗至德宗时代,陆续被称为“阿爸木比塔”、“阿巴白构”、“智改巴”的羌人部落的不断进攻而战败,迁居今马尔康县梭磨河流域,与白男(钵南)羌杂居,合为哥邻羌,[7](P132—133)为吐蕃属国。贞元后,哥邻羌董氏一部复内徙今理县境。笔者之所以把戈人被羌人击败而西迁一事系于唐代,是考虑到传说中的“阿巴白构”、“智改巴”等原来也住在“热兹”,即今松潘—若尔盖草原地带,并且以居帐蓬、营畜牧为生,[9]他们受“魔兵”驱赶进入会(茂)州境的过程,与唐中期赐支河曲、弱水西山羁縻州羌人部落受吐蕃侵略而内迁茂州的过程极为相似。唐代河曲、弱水及西山羌人大量迁入茂州河谷是见于史籍的而后来再没有过的重大民族迁移事件,从民俗学观点看,羌族民间传说《羌戈大战》有不少比较具体详细的情节,如果它反映的只是事属渺茫的上古汉代故事,而不是有史可稽的中古唐代故事,是不合情理的。另外,哥邻的立国约在武后时代,也与戈人(葛延)开始西迁的时间相吻合。
葛延羌未西迁前,《羌戈大战》将其描述为:“葛族知用牛曳犁耕田,……葛善治水,……葛有大量田土,智贫而无地。智向葛借粮食,借一斗,加五升之利。”羌人(智改巴)住山巅,戈人住岩脚;羌、戈双方都使用刀、矛、剑、戟和弓、矢等金属武器作战。各地羌民还传说,戈人身材高大,死后用石棺,制棺的青石从雪山运来,岷江和杂谷河流域的石棺坟便是戈人的坟墓,里面的陶罐,就是戈人留下的。1938年曾在汶川县威州北发掘过一个石棺墓,墓里的殉葬品有斧、戈、剑、带钩、钮扣、缨座子等铜器,有剑、矛、斧、刀、锯等铁器,又有铜柄铁剑、琉璃珠、银护腕、盾上连珠纽饰、榆荚钱和四铢钱等,[10](P169—171)证实上述传说确有一定真实性。人们曾认为此“戈人”文化应属于古蜀“纵目人”文化,亦即“氐羌”文化,“戈人”即《华阳国志》中的“作氐”,这恐非无稽之谈。然而石棺墓制度在东汉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墓主的消失,墓主如果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汉文化),未尝不可以改变自己文化中的某些制度如丧葬制度,从而使自己的文化得到升华,种族得以延续,所以前面提到的那种以为石棺墓的消失即是戈人末日的观点,未必成立。葛延羌作为氐羌,从广义上讲亦羌类,列之于诸羌也未尝不可,但总的来说,汉唐时代的葛延羌显然已是农耕民族,蔚然独秀,是诸羌中最先进最发达的一类。
五、向人羌《四川通史》谓其即唐初茂州都督府羁縻向州部落,在今理县西南。笔者赞同其说,但不同意所定方位,而认为应在今茂县东北及北川县西北一带,因为据《旧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所载里距推算,向州距茂州仅有三十里。向人羌后来也成为茂州羌之一部。
六、望族羌“望族”,《隋书·崔仲方传》作“望方”。“族”与“方”在古汉语中都可用于对边疆部族的通称,如上古之鬼方、羌方是也。《四川通史》谓其在今四川金川县西部一带,然未详其理由。笔者以为仲方军活动范围不会离会州太远,且金川县西部乃弱水羌之所在,故推测望族羌当在今汶川县北部,即隋唐之际会州汶川县羌人部落,后为茂州羌之一部。其名“望”,疑与汉扬雄《蜀王本纪》所谓“望帝升西山隐焉”有关,该部落有可能托名为古望帝之裔。望族羌地近葛延,居河谷,畜牛马,善治索桥,亦疑属氐羌类。《元和志》云:汶川县北三里有绳桥,架大江水,篾笮四条,以葛藤络,布板其上,虽从风摇动,而牢固有馀,夷人驱牛马来去无惧。
七、林台羌有拟音为rangdeg(朗德格),定在今四川德格县境者。按《隋书·崔仲方传》所列诸羌皆不出西山、弱水之间,今林台羌忽在数千里外之金沙江畔,实属可疑。《四川通史》疑即临涂羌,唐置为羁縻涂州,在今汶川县境,可从。后内徙茂州,亦为茂州羌之一部。
八、紫祖羌诸家未释。按《汉书·地理志》,绵水出紫岩山,又据《华阳国志·汉中志》,阴平郡有紫羌,笔者怀疑隋代紫祖羌即晋代紫羌,因紫岩山(今龙门山中段)为名(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166页云:“紫羌,盖喜穿紫色衣服,故名。”亦为一说),在今茂县东部、北川县西部及平武县南部一带,他们是隋唐之际会州北川、石泉2县的羌人部落,距会州州治最近,故隋时崔仲方讨会州诸叛羌从紫祖开始。唐中叶后,紫祖羌亦融入茂州羌。
九、四邻羌诸家未释。马长寿先生以“四邻”与“紫祖”连读,谓望方以下皆紫祖之四邻部落。[10](P182)按望方以下之诸部涉及岷江上游至大渡河中上游广大地区,紫祖一部本非大族,其四邻部落必不至牵连如此之广、如此之众。且崔仲方击紫祖四邻部落而不击紫祖本部,又有何益?故可断“四邻”与“紫祖”连读非是。考唐贞观初年以临涂羌复置之羁縻涂州有悉怜县,“悉怜”当即“四邻”之异译,隋崔仲方击破四邻羌,其残部归附于临涂羌,入唐,得为县。临涂羌,即前所谓“林台羌”。
十、白狗羌由于《旧唐志》有“武德〔七〕(元)年,白狗羌降附,乃于姜维故城置维州”,《元和志》有“茂州通化县(治今理县通化区)近白狗生羌”的明确记载,所以多数意见认为隋唐之际的白狗羌在今理县境,武德七年以其地置羁縻维州。但对贞观以后白狗羌的去向,却有一些争议。或以为贞观元年维州白狗羌叛,举族西走;或以为白狗羌向整个岷江西山地区扩展,以至于现代茂汶羌族基本上都是白狗羌的后裔。笔者以为前说之失在于不清楚武德七年以白狗羌为主体设置的羁縻笮州至广德年间一直存在于今理县境,贞观元年邓贤佐部西迁并不代表整个白狗羌西迁;后者之失在于未能证明“羌戈大战”的进攻方(即胜利方)只有白狗羌,尽管在有的地区的传说中进攻方确叫“阿巴白构”(据罗世泽调查),但有的地区却叫“智改巴”(据马长寿理县佳山寨调查),有的地区则叫“阿爸木比塔”(据汶川雁门乡调查),说明《羌戈大战》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作为进攻方的羌人应有多种,未可偏执一辞。其实仅从笮州长期存在于今理县境这一点看,就可知白狗羌主体基本未动,只是贞元九年以后弱水西山地区白狗国内附,行保州(在今理县东)又增加了一些白狗羌部落民而已。白狗羌居维州、笮州,产牦牛、麝香、羌活、当归(据《通典》卷六《食货六》、《元和志》及《新唐志》维州维川郡条)。其风俗,《隋书》云:“地本氐羌,人犹劲悍,性多质直,工习射猎。”《郡国志》云:“衣褐羊皮、革玄革各,妇人多带金花,串以〔瑟〕(琴)瑟,穿悬珠以为饰。”(《舆地纪胜》威州条引)反映其生活仍以畜牧狩猎为主。又以笮州州名观之,白狗羌亦当善治笮桥。唐时维、笮二州白狗羌首领俱姓邓氏。[11]
十一、涉题羌诸家未释。考唐贞观年间所置当州西境有悉唐川,在今四川黑水县西部黑水河流域,后置为悉唐县并静州、恭州
1
2 3
4
(鸣谢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
|